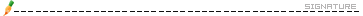我坐在Pub的一个角落啜着Tequila Sunrise,静静看着在光影眩目的舞池中、干冰挥发成的烟云中摇摆的灵魂,一个个像是挣扎不休、咆哮着的野兽。
我经常到这儿来,尤其假日前一晚更是风雨无阻,但从不曾下去舞池跳过,只是纯粹坐着、看着。
我曾经思索过自己这种无疑是浪费生命的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,或因什么造成,但一直无所获……换个方式说吧,
我想出来的理由,自个儿总是不以为然。
黄汤下肚,我习惯来根烟,自衬衫口袋掏出David Duff含一根到嘴里,却摸遍全身找不到打火机。
正想起身到吧台要盒火柴,一只属于女人的纤细的手伸到我面前,掌上放了 一个漂亮的火柴盒。「谢谢。」
我伸手要取,她却曲起手指收回。这人八成是想引我注意,而我也不好令她失望,于是抬头看她。由于Pub内灯光不甚明亮,我只看到她的浓妆艳抹:蓝黑色的眼影、火红的唇膏,以及太厚的粉底,看不真切她该是几岁或漂不漂亮。 她摊出另一手掌,弯起嘴唇笑说:「一根火柴一块钱。」声音俏皮而清亮。
当然,我可以不理会她的勒索,到隔壁桌借个火,或在吧台拿一盒免费付了她一元。
她把钱收到口袋里再拿出火柴来,弯身帮我点燃香烟。我这时看清楚了她的脸,发现她的妆涂得很不均匀,技巧之烂其实和她的穿著「很配」,还有,年龄。她点烟的动作很不俐落,甚至算得上笨拙,还微微发抖,应该不常做这种事。
如我所料的,「交易」完后她没有马上离开,反而在我对面坐了下来,还径自拿起我的酒凑到嘴边。她先是抿了一口,皱紧五官说:「真难喝。」又喝了一口才放下杯子。接着她又抽了根我的烟装模作样地啵了一口,假装吞云吐雾。
「抽烟又喝酒,你在自杀。」她直视着我说,眼神有些责备的味道。
我笑了出来,她这样子简直就像是以老师为偶像的好学生,
是的,她还是个孩子,依我猜,八成不超过十八岁。
「你的老师有没有告诉你,三更半夜不睡觉,同样会照成身体负担?」我端起酒,避开杯缘的唇印,仰头饮尽。「不爱惜身体并不表示不想活。」
她狡黠地笑笑。「真是『知其不可而为』呀。」我也回她一个笑容。
她见我起身,跟着站起来,尾随在后,仿佛赖定我了。
我坐上吧台前,她也在我旁边落坐。
「一杯Martini。」
「两杯。」她似乎不知客气为何物。
酒保看了看我,征询我的意见。我点点头。
「你都这样让女人予取予求吗?」她反倒像是不赞同我的慷慨。
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」我只是随口说说,并没有讨好她的意思,事实上,我比较想劝她回家睡觉。
「为什么希望我喜欢?」显然她不懂察颜观色。
「这样才有后续发展。」我故意以暧昧的眼神看她,和她对望了几秒。
「其实就算你不这么做,我也早决定今晚跟定你了。」她似乎不打算喝酒,只是用手指刮着杯子表面的水珠玩。 闻言,我差点将酒喷出。老实说,我并不认为这是飞来艳福,反倒是横 祸一场比较有可能──我可能会被告诱拐未成年少女。
见我吃惊,她轻笑了声,颇有恶作剧得逞的味道。
我喝完了酒,她果然跟在我屁股后面离开Pub。
「你不怕我对你怎样吗?」我想提醒她一点身为女人该有的警觉。
「你会对我怎样吗?」她笑着反问。
也许我该装出一副垂涎的恶态来吓唬她,教她别这么胆大妄为,可是,我得承认,
她看人的眼光不差──我是很尊重女性的。见我哑然以对,她快乐地勾住我的手。
「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。」「为什么?」走就是了。」她拖着我前进。
「喂,不会吧,你要用走路过去?很远耶。」
「反正人生还很漫长嘛。」
我觉得她这话似乎另藏含意,但我不是个追根究底的人,所以也就不问多。
「你有没有看过流星?」她突然仰起头,搜寻着天空问我。
「学生时代看过几次。往这边才对。」我拉着她左转。
「当时你有许愿吗?」
「有。」
不管是不是基于浪漫,我想每个人都有希冀实现的愿望,而一旦向宇宙的殒石许了愿就能不劳而获或得神助,何乐而不为?
「实现了吗?」
「实现的也成过去了。」
「瞧你说得悲伤的。你有心事?」她改看向我。
「你没心事?」
她顿了一下,「建议」地说:「你可以告诉我,」诱惑着,「我保证不会泄密。」
「我看起来像是个有苦无处申的人吗?」
「只是一脸『心事谁人知』而已。」她大概是信笃「『糗』人为快乐之本」。
我抹抹脸,有种想掩饰的心态。
「我去买个饮料。」她没追问,像是为了解我尴尬似的,看到前头有片便利商店的招牌便跑了过去。
到了公园,她欢呼了声,如飞出笼的小鸟,往公园深处奔去。她回头向我招手,催我赶快,但我仍自顾以原本的步伐走着。
她在露天表演台的对面草地停住,坐了下来喝饮料,顺便等我。
「你老了。」她喘着气取笑我的慢动作,拍拍身边意示我坐下。
「本来就不及你年轻。」我已经快三十了。「现在要干嘛?」
「想不想许愿?」
「妳想等流星?这里恐怕不容易看得到,光害太强了。」
她神秘兮兮地笑,「我们自己制造。」翻开包包,从中拿出一把冲天炮。
这下我终于明白她是早计划好了。
她一口饮尽剩余的饮料,把空罐摆到地上,抽出一枝冲天炮插进去。
「你想许什么愿?」她边说边掏出之前的火柴盒。
「天下太平好了。」我意兴阑珊。
「好。」
她二话不说,擦亮火柴点燃引信。
冲天炮咻地飞空,没有爆出巨响就在黑夜中化作缤纷绚烂。
「我很有道德感吧,特地选这种没有爆炸声的。」
我心里突然一阵感动,觉得刚才的愿望似乎受到了祝福,未来将是一片美丽。
「还有呢?」她已经准备好第二枝。
我兴致勃勃,也凑到饮料罐前。「我要环游全世界!」
「喔,好贪心。先说一个国家就好,简单的资料总是会被优先处理不是?」
「好,那么我要先到英国游泰晤士河!」
她又帮我把第二个愿望点燃,送进夜空。
「再到日本富士山滑雪!」我又喊。
她又摩擦第三根火柴。
「还要到法国看铁塔!」
「到德国拿一块柏林围墙的砖块!」
「到撒哈拉沙漠找小王子!」
我兴奋地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说下去,几乎把全世界说遍了。
「再来呀。」她鼓励着。
「呃,换你了。」我回过神时她手上的冲天炮只剩两枝。
「我的愿望只有一个,所以你还有一次机会。」
「怎么会只有一个呢?」
「我知足呀。快点。」
「好吧。我希望天下每个人都幸福美满!」
我的最后一个愿望也在她手下升空。
「我呢,」她顿了一下,偏头确定我正看着她才说下去,「希望你能永远记得我。」
接着把最后一枝火柴点燃。
空中又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。
「为什么希望我记得你?」我震惊于她刚才的话,久久不能平复。
「放心,我对你没有任何意图,只是希望多一个人记得我。」
「你这话听起来很……悲情。」
「会吗?」她低头笑了声。「你有没有想过,这世界除了你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外,
有谁会记得你一辈子?」我再度无言以对。
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,最后发现自己是个不容易被记忆的人,往往我一转身,一个月、半年过后,没人会再想起我。
这也许是与我太安静有关,然而,我该说什么呢?我该做什么呢?才能让别人也注意到我的存在?
「我有时会想,这个世界这么广大、人口这么多,有天我离开了、死了,有谁会注意到?十年、二十年之后,又还有谁会记得我?恐怕是根本没人知道我曾经存在过吧。
还有,我独处的时候就会想,也许我只是某一个人梦中的过路人,
只是虚幻的,只要那个人一醒,我就烟消雾散了。」
她抬头对我笑笑,有些羞赧。
「我唯一想得到证明自己真实存在的方法就是让别人记得我。当然啦,你也顶多记得我几十年,可是,我也没办法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让人编入历史课本中,也只好满足了。」 她这席话本说得有些哀伤,但在结尾时她俏皮地皱皱鼻,又把气氛带高。
「那么你下次可以找更年青的人,教他们制造流星,一定可以被记得更 久。」
她像是没听见我说话,兀自低头拿出火柴盒和一块钱,把钱放进盒里。「送 你。」
「为什么?」
「这样才能睹物思人啊。」她笑得开怀极了。
已届黎明了,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刻,我们为了取暖坐得很近,几乎相拥在一起,一股药味隐隐浮动在我鼻端。
「妳正在生病?」
「嗯。」
「那你应该在家休息才对。」
「没关系。」她搧搧手,突然仰起头看星空,抱怨似地说:
「台湾为什么 不会下雪呢?」
「因为纬度太低了。」
「今夜如果下雪,我会请你跳支华尔滋。」
我脑海中依着她的话勾勒出一幅我和她在雪中、星空下漫舞的美丽画面。
「没下雪也可以跳啊。」我边说边要站起,她却摇了摇头拒绝。
「我不会跳舞。」
「那你还说?」
「因为台湾不可能下雪。」她把脸埋进我颈窝。
「我困了,你的肩膀借一 下。」
我于是抱着她不动,任露水湿了屁股,直到天边灰蒙蒙地亮了,公园渐渐有人走动,
我才拍了拍她,「起来,回家睡去。喂!」气温太低了,我吐出来的呼吸都成了白烟。
她头还枕在我肩上,但右手有了动作使我知道她醒了。我推开她,却见她皱着五官,右手抓在左胸前,很痛苦似的。
「怎么了?」
「送我……到仁和医……院。」她呼出的白雾迷蒙了我的视线,待烟消雾尽我才看清她已快昏厥了。
我抱起她冲向公园门口,在路边招到一辆出租车,催促司机加快速度。
明明很冷的,但她的额头、脖子、手心却汗涔涔,妆也糊了。一路上,我抱着她,手不自主地发抖,不时探探她的鼻息,深怕她无声无息地「睡」去。
「撑着!」我在她耳边不停地说,可是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终于看见医院的招牌了,我丢下两百块,又抱着她跑起百米;从大门到大楼之的庭院间,
几名医护人员匆匆与我擦肩而过,加重了我的紧张。
进了医院内部,我一呼:「急诊」,两名护士迅速地推来病床,
她们一看我放下的病人,欢呼了起来。
「找到了,找到了,快去通知医生和她父母。」看起来较年长的护士指使着正巧经过的护士说,然后和另一位合作将她推进急诊室。
原来她是这里的「常客」。我心口稍微一松,抹抹脸,在急诊室外的椅子坐了下来。
约过了五分钟,一对男女慌慌张张跑到急诊室门口,望着那块发光的牌子,着急地双手互握。过了一会儿,男的发现了我,向我走来。
「是你送小女回来的?」
噗通!噗通!噗通!我其实听不太清楚男人说了什么,因为耳边有太多模糊的哭声、匆促脚步声、轮轴摩擦声、谈话声,以及很大的心跳声──不知是谁的心脏,竟如此有力──我很努力地分辨他张合的嘴唇,依稀猜出他说了什么。
见我点头,他躬了身,「谢谢。」马上走回女人身边。
好似在这张椅上过了下半辈子了,我看了第n 次表,才发现其实只过了十多分钟。
终于灯熄了,门开了,医师率先走出来,她父母一见就迎了上去。
「怎样?有没有怎样?」
「没事了。」医师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容。
很快的,护士们也把她推出来,我和她父母亦步亦趋地跟着,跟到病房前,其中一名护士把我们拦在门口。
「病人需要休息,别吵醒她。」
我们赶紧点头答应,待要进入,再出来的护士又挡住了我们。
「病人醒了,她说要见送她回来的那位先生。」
然后我在她父母奇异的注视下进了病房。
一见我进来,她虚弱地笑开来,指着墙壁说:「你看,这房间像不像被雪覆盖?」
她的妆已被洗净,脸色苍白得可怕。我随着她的指头将病房环视一圈,「嗯。」
「可惜我没力气了,不然就请你教我跳舞。」
「还有机会。」
她摇了摇头。「我今天就要飞往英国等动手术,不管有没有成功,都不会再回来了。」
我错愕,「你……」
「你知道吗?医院才是我的家,我一出生就住在这里了,反而父母住的地方没回去几次,我没上过学,没有交过其它朋友。」
我心疼她的遭遇,然而她却还是微笑着。「我离开后,台湾上会记得我的人就只有你了。」
「为什么是我?」
她先是怔然望着我,像是不懂我的问题,但很快又绽出笑容。
「在Pub里,你看起来像是冷眼旁观,但其实你很想融入他们,可是却没有勇气。你跟我一样,很多事情想做却又不敢做。」
「妳不是不敢,是不能。」
「谢谢你的安慰,可是我自己知道。你自己也知道的,对不对?」我默然。
「对不起,我累了。」她笑着下逐客令。
「那妳好好休息。」
我们没有说再见,因为明白不可能再见了。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「说完了。」我合上童话书,冲着三岁大的女儿笑,却发现她目瞪口呆地望着我,
突然,她哇地一声哭出来,跳下椅子抢过我手上的书本,边叫边跑出书房。
「妈妈,爸爸骗人……」我听见了妻子哄骗女儿的声音,所以就不追出去了。
我*入椅背,拉开桌子右边第二个抽屉,拿出一个漂亮却老旧的火柴盒,推开里盒,里头静躺着一枚硬币。
我一直努力着那晚所许的愿望,而至今只一个正被实行着,至于其它的,我想,正如她所说的,人生还很漫长。
不到别离,不知道爱有多深............
我经常到这儿来,尤其假日前一晚更是风雨无阻,但从不曾下去舞池跳过,只是纯粹坐着、看着。
我曾经思索过自己这种无疑是浪费生命的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,或因什么造成,但一直无所获……换个方式说吧,
我想出来的理由,自个儿总是不以为然。
黄汤下肚,我习惯来根烟,自衬衫口袋掏出David Duff含一根到嘴里,却摸遍全身找不到打火机。
正想起身到吧台要盒火柴,一只属于女人的纤细的手伸到我面前,掌上放了 一个漂亮的火柴盒。「谢谢。」
我伸手要取,她却曲起手指收回。这人八成是想引我注意,而我也不好令她失望,于是抬头看她。由于Pub内灯光不甚明亮,我只看到她的浓妆艳抹:蓝黑色的眼影、火红的唇膏,以及太厚的粉底,看不真切她该是几岁或漂不漂亮。 她摊出另一手掌,弯起嘴唇笑说:「一根火柴一块钱。」声音俏皮而清亮。
当然,我可以不理会她的勒索,到隔壁桌借个火,或在吧台拿一盒免费付了她一元。
她把钱收到口袋里再拿出火柴来,弯身帮我点燃香烟。我这时看清楚了她的脸,发现她的妆涂得很不均匀,技巧之烂其实和她的穿著「很配」,还有,年龄。她点烟的动作很不俐落,甚至算得上笨拙,还微微发抖,应该不常做这种事。
如我所料的,「交易」完后她没有马上离开,反而在我对面坐了下来,还径自拿起我的酒凑到嘴边。她先是抿了一口,皱紧五官说:「真难喝。」又喝了一口才放下杯子。接着她又抽了根我的烟装模作样地啵了一口,假装吞云吐雾。
「抽烟又喝酒,你在自杀。」她直视着我说,眼神有些责备的味道。
我笑了出来,她这样子简直就像是以老师为偶像的好学生,
是的,她还是个孩子,依我猜,八成不超过十八岁。
「你的老师有没有告诉你,三更半夜不睡觉,同样会照成身体负担?」我端起酒,避开杯缘的唇印,仰头饮尽。「不爱惜身体并不表示不想活。」
她狡黠地笑笑。「真是『知其不可而为』呀。」我也回她一个笑容。
她见我起身,跟着站起来,尾随在后,仿佛赖定我了。
我坐上吧台前,她也在我旁边落坐。
「一杯Martini。」
「两杯。」她似乎不知客气为何物。
酒保看了看我,征询我的意见。我点点头。
「你都这样让女人予取予求吗?」她反倒像是不赞同我的慷慨。
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」我只是随口说说,并没有讨好她的意思,事实上,我比较想劝她回家睡觉。
「为什么希望我喜欢?」显然她不懂察颜观色。
「这样才有后续发展。」我故意以暧昧的眼神看她,和她对望了几秒。
「其实就算你不这么做,我也早决定今晚跟定你了。」她似乎不打算喝酒,只是用手指刮着杯子表面的水珠玩。 闻言,我差点将酒喷出。老实说,我并不认为这是飞来艳福,反倒是横 祸一场比较有可能──我可能会被告诱拐未成年少女。
见我吃惊,她轻笑了声,颇有恶作剧得逞的味道。
我喝完了酒,她果然跟在我屁股后面离开Pub。
「你不怕我对你怎样吗?」我想提醒她一点身为女人该有的警觉。
「你会对我怎样吗?」她笑着反问。
也许我该装出一副垂涎的恶态来吓唬她,教她别这么胆大妄为,可是,我得承认,
她看人的眼光不差──我是很尊重女性的。见我哑然以对,她快乐地勾住我的手。
「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。」「为什么?」走就是了。」她拖着我前进。
「喂,不会吧,你要用走路过去?很远耶。」
「反正人生还很漫长嘛。」
我觉得她这话似乎另藏含意,但我不是个追根究底的人,所以也就不问多。
「你有没有看过流星?」她突然仰起头,搜寻着天空问我。
「学生时代看过几次。往这边才对。」我拉着她左转。
「当时你有许愿吗?」
「有。」
不管是不是基于浪漫,我想每个人都有希冀实现的愿望,而一旦向宇宙的殒石许了愿就能不劳而获或得神助,何乐而不为?
「实现了吗?」
「实现的也成过去了。」
「瞧你说得悲伤的。你有心事?」她改看向我。
「你没心事?」
她顿了一下,「建议」地说:「你可以告诉我,」诱惑着,「我保证不会泄密。」
「我看起来像是个有苦无处申的人吗?」
「只是一脸『心事谁人知』而已。」她大概是信笃「『糗』人为快乐之本」。
我抹抹脸,有种想掩饰的心态。
「我去买个饮料。」她没追问,像是为了解我尴尬似的,看到前头有片便利商店的招牌便跑了过去。
到了公园,她欢呼了声,如飞出笼的小鸟,往公园深处奔去。她回头向我招手,催我赶快,但我仍自顾以原本的步伐走着。
她在露天表演台的对面草地停住,坐了下来喝饮料,顺便等我。
「你老了。」她喘着气取笑我的慢动作,拍拍身边意示我坐下。
「本来就不及你年轻。」我已经快三十了。「现在要干嘛?」
「想不想许愿?」
「妳想等流星?这里恐怕不容易看得到,光害太强了。」
她神秘兮兮地笑,「我们自己制造。」翻开包包,从中拿出一把冲天炮。
这下我终于明白她是早计划好了。
她一口饮尽剩余的饮料,把空罐摆到地上,抽出一枝冲天炮插进去。
「你想许什么愿?」她边说边掏出之前的火柴盒。
「天下太平好了。」我意兴阑珊。
「好。」
她二话不说,擦亮火柴点燃引信。
冲天炮咻地飞空,没有爆出巨响就在黑夜中化作缤纷绚烂。
「我很有道德感吧,特地选这种没有爆炸声的。」
我心里突然一阵感动,觉得刚才的愿望似乎受到了祝福,未来将是一片美丽。
「还有呢?」她已经准备好第二枝。
我兴致勃勃,也凑到饮料罐前。「我要环游全世界!」
「喔,好贪心。先说一个国家就好,简单的资料总是会被优先处理不是?」
「好,那么我要先到英国游泰晤士河!」
她又帮我把第二个愿望点燃,送进夜空。
「再到日本富士山滑雪!」我又喊。
她又摩擦第三根火柴。
「还要到法国看铁塔!」
「到德国拿一块柏林围墙的砖块!」
「到撒哈拉沙漠找小王子!」
我兴奋地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说下去,几乎把全世界说遍了。
「再来呀。」她鼓励着。
「呃,换你了。」我回过神时她手上的冲天炮只剩两枝。
「我的愿望只有一个,所以你还有一次机会。」
「怎么会只有一个呢?」
「我知足呀。快点。」
「好吧。我希望天下每个人都幸福美满!」
我的最后一个愿望也在她手下升空。
「我呢,」她顿了一下,偏头确定我正看着她才说下去,「希望你能永远记得我。」
接着把最后一枝火柴点燃。
空中又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。
「为什么希望我记得你?」我震惊于她刚才的话,久久不能平复。
「放心,我对你没有任何意图,只是希望多一个人记得我。」
「你这话听起来很……悲情。」
「会吗?」她低头笑了声。「你有没有想过,这世界除了你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外,
有谁会记得你一辈子?」我再度无言以对。
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,最后发现自己是个不容易被记忆的人,往往我一转身,一个月、半年过后,没人会再想起我。
这也许是与我太安静有关,然而,我该说什么呢?我该做什么呢?才能让别人也注意到我的存在?
「我有时会想,这个世界这么广大、人口这么多,有天我离开了、死了,有谁会注意到?十年、二十年之后,又还有谁会记得我?恐怕是根本没人知道我曾经存在过吧。
还有,我独处的时候就会想,也许我只是某一个人梦中的过路人,
只是虚幻的,只要那个人一醒,我就烟消雾散了。」
她抬头对我笑笑,有些羞赧。
「我唯一想得到证明自己真实存在的方法就是让别人记得我。当然啦,你也顶多记得我几十年,可是,我也没办法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让人编入历史课本中,也只好满足了。」 她这席话本说得有些哀伤,但在结尾时她俏皮地皱皱鼻,又把气氛带高。
「那么你下次可以找更年青的人,教他们制造流星,一定可以被记得更 久。」
她像是没听见我说话,兀自低头拿出火柴盒和一块钱,把钱放进盒里。「送 你。」
「为什么?」
「这样才能睹物思人啊。」她笑得开怀极了。
已届黎明了,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刻,我们为了取暖坐得很近,几乎相拥在一起,一股药味隐隐浮动在我鼻端。
「妳正在生病?」
「嗯。」
「那你应该在家休息才对。」
「没关系。」她搧搧手,突然仰起头看星空,抱怨似地说:
「台湾为什么 不会下雪呢?」
「因为纬度太低了。」
「今夜如果下雪,我会请你跳支华尔滋。」
我脑海中依着她的话勾勒出一幅我和她在雪中、星空下漫舞的美丽画面。
「没下雪也可以跳啊。」我边说边要站起,她却摇了摇头拒绝。
「我不会跳舞。」
「那你还说?」
「因为台湾不可能下雪。」她把脸埋进我颈窝。
「我困了,你的肩膀借一 下。」
我于是抱着她不动,任露水湿了屁股,直到天边灰蒙蒙地亮了,公园渐渐有人走动,
我才拍了拍她,「起来,回家睡去。喂!」气温太低了,我吐出来的呼吸都成了白烟。
她头还枕在我肩上,但右手有了动作使我知道她醒了。我推开她,却见她皱着五官,右手抓在左胸前,很痛苦似的。
「怎么了?」
「送我……到仁和医……院。」她呼出的白雾迷蒙了我的视线,待烟消雾尽我才看清她已快昏厥了。
我抱起她冲向公园门口,在路边招到一辆出租车,催促司机加快速度。
明明很冷的,但她的额头、脖子、手心却汗涔涔,妆也糊了。一路上,我抱着她,手不自主地发抖,不时探探她的鼻息,深怕她无声无息地「睡」去。
「撑着!」我在她耳边不停地说,可是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终于看见医院的招牌了,我丢下两百块,又抱着她跑起百米;从大门到大楼之的庭院间,
几名医护人员匆匆与我擦肩而过,加重了我的紧张。
进了医院内部,我一呼:「急诊」,两名护士迅速地推来病床,
她们一看我放下的病人,欢呼了起来。
「找到了,找到了,快去通知医生和她父母。」看起来较年长的护士指使着正巧经过的护士说,然后和另一位合作将她推进急诊室。
原来她是这里的「常客」。我心口稍微一松,抹抹脸,在急诊室外的椅子坐了下来。
约过了五分钟,一对男女慌慌张张跑到急诊室门口,望着那块发光的牌子,着急地双手互握。过了一会儿,男的发现了我,向我走来。
「是你送小女回来的?」
噗通!噗通!噗通!我其实听不太清楚男人说了什么,因为耳边有太多模糊的哭声、匆促脚步声、轮轴摩擦声、谈话声,以及很大的心跳声──不知是谁的心脏,竟如此有力──我很努力地分辨他张合的嘴唇,依稀猜出他说了什么。
见我点头,他躬了身,「谢谢。」马上走回女人身边。
好似在这张椅上过了下半辈子了,我看了第n 次表,才发现其实只过了十多分钟。
终于灯熄了,门开了,医师率先走出来,她父母一见就迎了上去。
「怎样?有没有怎样?」
「没事了。」医师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容。
很快的,护士们也把她推出来,我和她父母亦步亦趋地跟着,跟到病房前,其中一名护士把我们拦在门口。
「病人需要休息,别吵醒她。」
我们赶紧点头答应,待要进入,再出来的护士又挡住了我们。
「病人醒了,她说要见送她回来的那位先生。」
然后我在她父母奇异的注视下进了病房。
一见我进来,她虚弱地笑开来,指着墙壁说:「你看,这房间像不像被雪覆盖?」
她的妆已被洗净,脸色苍白得可怕。我随着她的指头将病房环视一圈,「嗯。」
「可惜我没力气了,不然就请你教我跳舞。」
「还有机会。」
她摇了摇头。「我今天就要飞往英国等动手术,不管有没有成功,都不会再回来了。」
我错愕,「你……」
「你知道吗?医院才是我的家,我一出生就住在这里了,反而父母住的地方没回去几次,我没上过学,没有交过其它朋友。」
我心疼她的遭遇,然而她却还是微笑着。「我离开后,台湾上会记得我的人就只有你了。」
「为什么是我?」
她先是怔然望着我,像是不懂我的问题,但很快又绽出笑容。
「在Pub里,你看起来像是冷眼旁观,但其实你很想融入他们,可是却没有勇气。你跟我一样,很多事情想做却又不敢做。」
「妳不是不敢,是不能。」
「谢谢你的安慰,可是我自己知道。你自己也知道的,对不对?」我默然。
「对不起,我累了。」她笑着下逐客令。
「那妳好好休息。」
我们没有说再见,因为明白不可能再见了。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「说完了。」我合上童话书,冲着三岁大的女儿笑,却发现她目瞪口呆地望着我,
突然,她哇地一声哭出来,跳下椅子抢过我手上的书本,边叫边跑出书房。
「妈妈,爸爸骗人……」我听见了妻子哄骗女儿的声音,所以就不追出去了。
我*入椅背,拉开桌子右边第二个抽屉,拿出一个漂亮却老旧的火柴盒,推开里盒,里头静躺着一枚硬币。
我一直努力着那晚所许的愿望,而至今只一个正被实行着,至于其它的,我想,正如她所说的,人生还很漫长。
不到别离,不知道爱有多深............